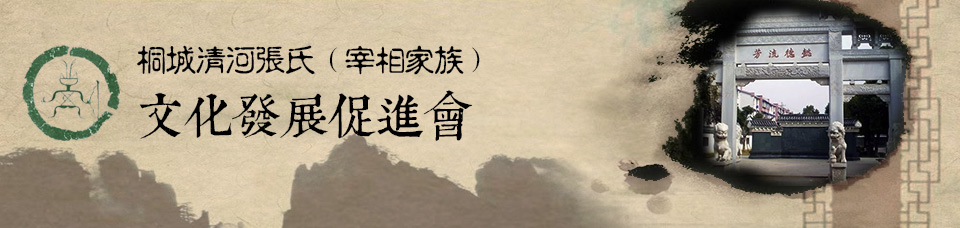族人今作
六尺巷人物杂忆
作者:admin 来源:本站点击数:3289
发布时间:2016-11-09
(一)焚书遥祭菡姐
梦魂昨夜到桐城,
故旧相扶竞出迎。
互贺白头犹健在,
梦魂昨夜到桐城,
故旧相扶竞出迎。
互贺白头犹健在,
也难笑里暗吞声。
多少夜寂人静之时,我捧出有“桐城才女”之称的台湾著名诗人、作家张淑菡的诗集《荷香集》,翻读其中的这首《梦中归里》,愈读愈觉清香四溢,愈读心情也愈沉重,每每彻夜难眠。
张淑菡是我的从堂姐。我们均系清朝宰相(保和殿大学士)张廷玉的九世孙。解放前同住“相府”(现为安徽省荣军康复医院,址在桐城市区)。她这个当年的“相府千金”(六小姐)在我众多的姐姐中,是最有魅力的才女,从小就表现出大家闺秀的风范。
因当年她的父亲(我的堂伯父)在故都北平(今北京)任职,她随父亲在那里求学,假期才得归里与我们团聚。时日不多,印象极深,有两件小事至今仍时常浮现眼前。
一件事是“新年提灯会”。1946年新年,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,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对国家统一复兴的期盼之中,新年十分热闹,为了打破“相府”内陈旧、沉闷的空气,菡姐姐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会。先是提灯游园,整个家族各房头的半大孩子,几乎倾巢而出,将近百人,一人一个,手提灯笼,灯笼造型异彩纷呈。游园从家庙开始,浩浩荡荡,一路光明,游遍相府每个角落,最后至大花园集中游戏、唱和。这次提灯游园,整个相府都惊动了,甚至还引来了四邻的众多居民。接着是摸摸奖,奖品有玩具、文具、书籍等。我当时才七岁,记得是摸了一件女孩子的饰物,惹得比我大的兄姐嘲笑:“小小年纪,爱上了女色,好一个贾宝玉!”当时年小,不懂什么,但知他们嘲笑我,羞得大哭起来。正在兴致勃勃主持摸奖的菡姐见状,立即前来抚慰,并送我一件精美的文具,鼓励我说:“小渝(我的乳名,因生于重庆而取)聪明,将来肯定能在学业上有出息!”我成人之后,也开始舞文弄墨,便想到这件事,不知其中可有因缘、预兆。
另一件事,是“怒斥花花姑(神婆)”。菡姐的母亲(我的堂大伯母)因不小心从楼梯上跌滚下来,大腿骨折,久治未愈,痛苦难受,日夜心惊肉跳,弄得整个相府不得安宁,一片阴森之气。家人迷信,便请“花花姑”前来卜算阴凶,除邪辟怪。“花花姑”说此屋里有“龌龊”(即鬼怪),必须由她乘八抬大轿出府,向南走七七四十九里,将所遇的一条黑狗逮回活活打死,用黑狗的血海洒楼梯上下、屋里屋外以驱怪,并设神坛念咒七七四十九天。家人如此照办,两位伙计将逮回的黑狗捆在大树上,一位用斧砍狗,一位跪在旁边向狗磕头如捣蒜,并喃喃而语:“神犬见谅,小人奉命行事,罪过罪过。”当时我站在一旁观看,黑狗的叫声十分凄厉,直至活活被砍死,令人惊恐万状。那次,恰逢菡姐放假回家,那“花花姑”正在屋内设坛装神弄鬼,下人一片虔诚。菡姐见之,不由分说,怒斥神婆,并将所有法器冥物尽皆抛弃于屋外。事后,她请来名医治好了母伤。此事在当时相府内着实引起了轰动,毁誉均有。今天回想起来,我对菡姐还是敬佩有加。
1948年,18岁的菡姐因陪伴母亲取道香港赴台观光,不料被突变的时局所滞,留在了台湾。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,族人才有机会与菡姐鸿雁传书,大陆也陆续有她的作品出版。晚年的她将自己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寄回家乡的“桐城文库”收藏。这时期,我们才知道她自离大陆后,一心扑在她所倾心的文学事业上,先后出版了《意难忘》等三十多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文学造诣很高的诗词作品,计有两千万字,成了台湾最负盛名的“为端正社会风气而写作”的作家,蜚声台湾文坛数十年。
菡姐晚年曾向族人寄回一首《怀乡》诗。诗曰:“新月如钩透碧纱,无端心系故园花。只恐梦魂飞不到,庭前双桂是吾家。”“只恐”之事在20世纪最后之际惊成现实,历经浩劫磨难的“庭前双桂”虽然依旧在,但其“梦魂”已永远“飞不到”“吾家”了。
半个多世纪,海天阻隔,姐弟也分阴阳之界。我只有将自己新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褒贬皆一笑》(内有与菡姐有关的文字)焚献南天,遥祭菡姐,以寄心香一瓣。
注:张淑菡于2000年6月17日下午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台北去世。终年70岁。
张淑菡是我的从堂姐。我们均系清朝宰相(保和殿大学士)张廷玉的九世孙。解放前同住“相府”(现为安徽省荣军康复医院,址在桐城市区)。她这个当年的“相府千金”(六小姐)在我众多的姐姐中,是最有魅力的才女,从小就表现出大家闺秀的风范。
因当年她的父亲(我的堂伯父)在故都北平(今北京)任职,她随父亲在那里求学,假期才得归里与我们团聚。时日不多,印象极深,有两件小事至今仍时常浮现眼前。
一件事是“新年提灯会”。1946年新年,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个新年,全国人民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与对国家统一复兴的期盼之中,新年十分热闹,为了打破“相府”内陈旧、沉闷的空气,菡姐姐组织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庆祝会。先是提灯游园,整个家族各房头的半大孩子,几乎倾巢而出,将近百人,一人一个,手提灯笼,灯笼造型异彩纷呈。游园从家庙开始,浩浩荡荡,一路光明,游遍相府每个角落,最后至大花园集中游戏、唱和。这次提灯游园,整个相府都惊动了,甚至还引来了四邻的众多居民。接着是摸摸奖,奖品有玩具、文具、书籍等。我当时才七岁,记得是摸了一件女孩子的饰物,惹得比我大的兄姐嘲笑:“小小年纪,爱上了女色,好一个贾宝玉!”当时年小,不懂什么,但知他们嘲笑我,羞得大哭起来。正在兴致勃勃主持摸奖的菡姐见状,立即前来抚慰,并送我一件精美的文具,鼓励我说:“小渝(我的乳名,因生于重庆而取)聪明,将来肯定能在学业上有出息!”我成人之后,也开始舞文弄墨,便想到这件事,不知其中可有因缘、预兆。
另一件事,是“怒斥花花姑(神婆)”。菡姐的母亲(我的堂大伯母)因不小心从楼梯上跌滚下来,大腿骨折,久治未愈,痛苦难受,日夜心惊肉跳,弄得整个相府不得安宁,一片阴森之气。家人迷信,便请“花花姑”前来卜算阴凶,除邪辟怪。“花花姑”说此屋里有“龌龊”(即鬼怪),必须由她乘八抬大轿出府,向南走七七四十九里,将所遇的一条黑狗逮回活活打死,用黑狗的血海洒楼梯上下、屋里屋外以驱怪,并设神坛念咒七七四十九天。家人如此照办,两位伙计将逮回的黑狗捆在大树上,一位用斧砍狗,一位跪在旁边向狗磕头如捣蒜,并喃喃而语:“神犬见谅,小人奉命行事,罪过罪过。”当时我站在一旁观看,黑狗的叫声十分凄厉,直至活活被砍死,令人惊恐万状。那次,恰逢菡姐放假回家,那“花花姑”正在屋内设坛装神弄鬼,下人一片虔诚。菡姐见之,不由分说,怒斥神婆,并将所有法器冥物尽皆抛弃于屋外。事后,她请来名医治好了母伤。此事在当时相府内着实引起了轰动,毁誉均有。今天回想起来,我对菡姐还是敬佩有加。
1948年,18岁的菡姐因陪伴母亲取道香港赴台观光,不料被突变的时局所滞,留在了台湾。
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之后,族人才有机会与菡姐鸿雁传书,大陆也陆续有她的作品出版。晚年的她将自己的大部分重要作品寄回家乡的“桐城文库”收藏。这时期,我们才知道她自离大陆后,一心扑在她所倾心的文学事业上,先后出版了《意难忘》等三十多部长、中、短篇小说以及大量的文学造诣很高的诗词作品,计有两千万字,成了台湾最负盛名的“为端正社会风气而写作”的作家,蜚声台湾文坛数十年。
菡姐晚年曾向族人寄回一首《怀乡》诗。诗曰:“新月如钩透碧纱,无端心系故园花。只恐梦魂飞不到,庭前双桂是吾家。”“只恐”之事在20世纪最后之际惊成现实,历经浩劫磨难的“庭前双桂”虽然依旧在,但其“梦魂”已永远“飞不到”“吾家”了。
半个多世纪,海天阻隔,姐弟也分阴阳之界。我只有将自己新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《褒贬皆一笑》(内有与菡姐有关的文字)焚献南天,遥祭菡姐,以寄心香一瓣。
注:张淑菡于2000年6月17日下午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台北去世。终年70岁。
(二)关于父亲的碎片
父亲离世已近一个花甲,从未在我的梦中出现。如今,我也是逼近古稀之人,常想为父亲写点什么。自写了《母亲的遗训》之后,这种写作欲望总是挥之不去。但当我展笺运笔之际,映现于脑海的全是关于父亲的一些碎片。我想,这“碎片”也是难得的材料,于是便记了下来,权当是对父亲的祭奠吧!
官宦世家的濡染,并没有使他养成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的“少爷”、“老爷”德性,更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那种斗鸡走狗、招摇过市的恶习。听老人们说父亲从小就非常勤勉、温驯与善良,从不对“下人”颐指气使。优良家教的传承,深厚国学的浸润,以及“五四”之后新思潮的熏陶,都使他有一身儒雅之气。学成之后,便毅然决然脱去长衫,走出“相府”,踏上了服务社会、报效国家、致力共和的人生之路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,他在国民政府的某一中央机构任职,抗战时期在重庆,胜利后在南京。清癯英俊,文质彬彬,戴着眼镜,一身戎装,便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初影像。
我在抗战中的“陪都”重庆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初六年。我唯一记得住的事便是“跑警报”,以躲避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。每当警报来时,父亲抱着我,母亲抱着弟弟,在卫兵及女佣人的护送下,前往指定的防空洞。那时难民多,专供一般百姓用的防空洞很少,难民不及躲避,被炸死的很多。父亲经常在途中,让卫兵和女佣将一时难以避炸的老人、妇女、小孩带进只有像父亲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去的防空洞。这在当时也是严重的“违规”行为。我不知道这可给父亲惹过麻烦,要有,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应付过去的。
父亲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高,又钻研过西洋文学。他懂法文,也擅长书画,他的书房成了我的乐园。在这里,我学前就知道了李白、杜甫,并且会背诵他们的很多诗。后来,父亲还为我订了《儿童良友》和《××少年》等新学报刊,指导我阅读,培养了我的读书习惯,使我最早知道了大、小仲马,也认识了“一个偷自行车的人”。这是父亲给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旧时家庭,财产纠纷司空见惯。母亲为此与有关族人严重失和。每当她们吵闹得天翻地覆之时,父亲与伯父兄弟俩总是若无其事地在房内或拉胡琴,或唱京剧,热火朝天,不亦乐乎,对房外的唇枪舌剑不屑一顾。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小时不懂,长大后经历多了,读书多了,对父亲这种豁达也就有了深层的感悟。
1946年底,父亲即辞官归里赋闲。有时也在张氏私办的学堂——“聪训小学”里教点国文课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父亲就开始酗酒。对此,母亲管得很严,父亲常趁着母亲暂时不在,甚至转背的瞬间,拿起酒瓶往嘴里咕噜咕噜倒酒。父亲还经常带着我在外面喝酒,每次都叮嘱我不要告诉母亲。其实,根本不用我告密,他每喝必醉,跌倒摔伤、丢失近视眼镜是常事,回家后必然受到母亲的呵斥,甚至耳光的教训。就是这样,父亲还是一年三百六十日,日日醉如泥。距他辞官回乡仅两年,就因酗酒成痨,咯血不止,药石无灵而亡,时年三十八岁。我才九岁。我长大之后,起始还惋惜他的英年早逝,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,我才知道,以父亲的家庭出身与本人的官位,虽说无罪恶、无民愤,且任职又是在国共合作期间,但在猖獗的左风之下,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的,以他那病弱之躯是绝对挺不过来的。所以我又很庆幸,觉得父亲是死得其时。
父亲死后,按习俗,也因时局,暂厝待葬。后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,尸骨不知去向。若干年前,有好心人找到我,说是我父亲残骸犹存,希望我兄弟俩能“捡金”重葬。我们去实地看过,其地并无坟地,也不知可有尸骨。即使有,也真假莫辨,认定和否定者都有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放弃了重葬的打算。说真的,我也不忍让父亲再死一回了!
官宦世家的濡染,并没有使他养成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的“少爷”、“老爷”德性,更没有一般纨绔子弟的那种斗鸡走狗、招摇过市的恶习。听老人们说父亲从小就非常勤勉、温驯与善良,从不对“下人”颐指气使。优良家教的传承,深厚国学的浸润,以及“五四”之后新思潮的熏陶,都使他有一身儒雅之气。学成之后,便毅然决然脱去长衫,走出“相府”,踏上了服务社会、报效国家、致力共和的人生之路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,他在国民政府的某一中央机构任职,抗战时期在重庆,胜利后在南京。清癯英俊,文质彬彬,戴着眼镜,一身戎装,便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初影像。
我在抗战中的“陪都”重庆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初六年。我唯一记得住的事便是“跑警报”,以躲避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。每当警报来时,父亲抱着我,母亲抱着弟弟,在卫兵及女佣人的护送下,前往指定的防空洞。那时难民多,专供一般百姓用的防空洞很少,难民不及躲避,被炸死的很多。父亲经常在途中,让卫兵和女佣将一时难以避炸的老人、妇女、小孩带进只有像父亲这样的人才可以进去的防空洞。这在当时也是严重的“违规”行为。我不知道这可给父亲惹过麻烦,要有,也不知道他当时是怎么应付过去的。
父亲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很高,又钻研过西洋文学。他懂法文,也擅长书画,他的书房成了我的乐园。在这里,我学前就知道了李白、杜甫,并且会背诵他们的很多诗。后来,父亲还为我订了《儿童良友》和《××少年》等新学报刊,指导我阅读,培养了我的读书习惯,使我最早知道了大、小仲马,也认识了“一个偷自行车的人”。这是父亲给我的最早的文学启蒙。
旧时家庭,财产纠纷司空见惯。母亲为此与有关族人严重失和。每当她们吵闹得天翻地覆之时,父亲与伯父兄弟俩总是若无其事地在房内或拉胡琴,或唱京剧,热火朝天,不亦乐乎,对房外的唇枪舌剑不屑一顾。这一幕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小时不懂,长大后经历多了,读书多了,对父亲这种豁达也就有了深层的感悟。
1946年底,父亲即辞官归里赋闲。有时也在张氏私办的学堂——“聪训小学”里教点国文课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父亲就开始酗酒。对此,母亲管得很严,父亲常趁着母亲暂时不在,甚至转背的瞬间,拿起酒瓶往嘴里咕噜咕噜倒酒。父亲还经常带着我在外面喝酒,每次都叮嘱我不要告诉母亲。其实,根本不用我告密,他每喝必醉,跌倒摔伤、丢失近视眼镜是常事,回家后必然受到母亲的呵斥,甚至耳光的教训。就是这样,父亲还是一年三百六十日,日日醉如泥。距他辞官回乡仅两年,就因酗酒成痨,咯血不止,药石无灵而亡,时年三十八岁。我才九岁。我长大之后,起始还惋惜他的英年早逝,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,我才知道,以父亲的家庭出身与本人的官位,虽说无罪恶、无民愤,且任职又是在国共合作期间,但在猖獗的左风之下,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的,以他那病弱之躯是绝对挺不过来的。所以我又很庆幸,觉得父亲是死得其时。
父亲死后,按习俗,也因时局,暂厝待葬。后因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,尸骨不知去向。若干年前,有好心人找到我,说是我父亲残骸犹存,希望我兄弟俩能“捡金”重葬。我们去实地看过,其地并无坟地,也不知可有尸骨。即使有,也真假莫辨,认定和否定者都有。在这种情况下,我们就放弃了重葬的打算。说真的,我也不忍让父亲再死一回了!
(《焚书遥祭菡姐》,原载于张先涛散文集《心之韵》,作家出版社出版。)
【打印】
上一篇:“让他三尺又何妨”
下一篇:没有了!